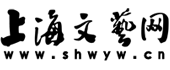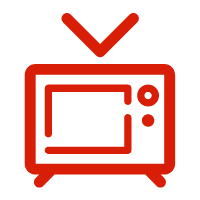我是個(gè)書(shū)法愛(ài)好者,總覺(jué)得古老的的書(shū)道不能完全承擔(dān)新時(shí)代書(shū)法教育之重;但又不見(jiàn)新時(shí)代書(shū)道的權(quán)威發(fā)布,故常到書(shū)市去尋找解決這一矛盾的答案。一天,在一家書(shū)店發(fā)現(xiàn)幾本《書(shū)法?國(guó)學(xué)》呆在那里,既無(wú)店長(zhǎng)推薦,又非名人所著。琢磨書(shū)名,“書(shū)法”“國(guó)學(xué)”兩個(gè)名詞由“?”聯(lián)結(jié),便覺(jué)出些“怪味”來(lái)。我是個(gè)怪人,就把這“怪味”的書(shū)帶回了家。事后,我桂花樹(shù)下讀此書(shū),花香、書(shū)香伴我一口氣讀完。然而也有些疑惑:幾個(gè)做基礎(chǔ)教育的先生能編著出這等味道的書(shū)來(lái)?這里有高度、深度、寬度、可讀度,更有新時(shí)代教育發(fā)展的戰(zhàn)略眼光啊!
高度,獨(dú)一味。
“讀出來(lái)是中國(guó)聲,擺出來(lái)是中國(guó)樣,品起來(lái)是中國(guó)味,蘊(yùn)涵的是中國(guó)情,給予的是中國(guó)力,在古今中外文化藝術(shù)中,唯有漢字書(shū)法!”
這是扉頁(yè)中的一段話(huà)。
書(shū)法,原本只是寫(xiě)字;高看了,只是藝術(shù)。但有誰(shuí)之前有過(guò)這種判斷呢!這一獨(dú)特的判斷竟然從書(shū)法藝術(shù)中讀出了中國(guó)聲音,看到了中國(guó)模樣,品到了中國(guó)味道,觸到了中國(guó)情感,碰到了中國(guó)力量!書(shū)法史上對(duì)書(shū)法本質(zhì)最高境界的判斷也只有孫過(guò)庭《書(shū)譜序》里的“達(dá)其情性,形其哀樂(lè)”啊!
這一判斷,準(zhǔn)確、新穎,然而又沒(méi)“失根”。清代學(xué)者梁松齋說(shuō):“晉尚韻,唐尚法,宋尚意,元、明尚態(tài)”;當(dāng)代學(xué)者蔣勛說(shuō):“學(xué)習(xí)直線(xiàn)的耿直,也學(xué)習(xí)曲線(xiàn)的婉轉(zhuǎn);學(xué)習(xí)‘方’的端正,也學(xué)習(xí)‘圓’的包容;東亞文化的核心價(jià)值,其實(shí)一直在漢字的書(shū)寫(xiě)中。”這不與他們的觀念不謀而合,基本相符嗎?梁公的話(huà),雖是對(duì)各朝各代書(shū)法崇尚點(diǎn)的的概括,但也可從“韻”、“意”、“態(tài)”等文眼,讀出中國(guó)特色的“聲”與“情”,看出“樣”與“力”,品出“韻味”。
“借著書(shū)法的階梯,登上國(guó)學(xué)的高臺(tái),鳥(niǎo)瞰書(shū)法秘笈;以國(guó)學(xué)為乳汁,以書(shū)法為奶頭,學(xué)書(shū)法,學(xué)國(guó)學(xué),學(xué)做人,一起為提高學(xué)生綜合素質(zhì)而動(dòng)!”
這是封底中的一段話(huà)。
書(shū)法教育,原本只是教人運(yùn)筆寫(xiě)字;高點(diǎn)說(shuō),只是教育學(xué)生學(xué)習(xí)書(shū)法技藝,成就一筆漂亮的字。可之前有誰(shuí)提出并實(shí)踐過(guò)學(xué)書(shū)法,學(xué)國(guó)學(xué),學(xué)做人呢?書(shū)法、國(guó)學(xué)、做人,原本分門(mén)別類(lèi),自成一家;然而《書(shū)法?國(guó)學(xué)》一書(shū),三者通識(shí)、通教、通學(xué)、通用,撞穿壁壘,學(xué)一點(diǎn),得一串,這不正是新時(shí)代教育的新思維、新舉措嗎?
蔣勛的話(huà)更加直接,從“直線(xiàn)的耿直”到“曲線(xiàn)的婉轉(zhuǎn)”,從“方的端正”到“圓的包容”,告訴人們:中國(guó)文化的核心價(jià)值,一直就在漢字的書(shū)寫(xiě)中。由此得知,漢字書(shū)法的“核心價(jià)值”絕不只是教人寫(xiě)一手漂亮的字吧!
本書(shū)高度的“獨(dú)一味”,絕非是一朝艷的曇花,而是中國(guó)本土長(zhǎng)青樹(shù)的新枝。早在幾千年前,我們的祖先就把“書(shū)”列在“六藝”與“六經(jīng)”內(nèi),無(wú)論哪一種(或禮、樂(lè)、射、御、書(shū)、數(shù)或《 詩(shī)》《 書(shū)》《 禮》《 易》《 春秋》《 樂(lè)》)都沒(méi)缺少過(guò)“書(shū)”;到了書(shū)法“完法”的晉代,王羲之說(shuō):“須得書(shū)意轉(zhuǎn)深,點(diǎn)畫(huà)之中皆有意”;到了“尚法”的唐朝,皇帝李世民都說(shuō):“書(shū),心畫(huà)也”。這“意”這“心”指什么?我們來(lái)個(gè)發(fā)散性思維,不難發(fā)現(xiàn),指國(guó)學(xué)——傳統(tǒng)文化。有人說(shuō):指書(shū)法家個(gè)人的思想感情。這沒(méi)錯(cuò),但個(gè)人的思想情感又怎能脫離得了傳統(tǒng)文化?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》第1卷第18頁(yè)中說(shuō):“人的本質(zhì)是一切社會(huì)關(guān)系的總和 ”。在看看實(shí)際的東西,經(jīng)歷史淘而沒(méi)汰,留名千古的書(shū)法家有哪一位不是滿(mǎn)腹經(jīng)綸的國(guó)學(xué)大師呢?即使有些沒(méi)讀過(guò)四書(shū)五經(jīng)六藝的書(shū)法子民,國(guó)學(xué)的潮汐就沒(méi)能打濕過(guò)他們的鞋?
如果說(shuō)把“書(shū)”歸為“六藝”,是宏觀的視野,那么王羲之“書(shū)意轉(zhuǎn)深”的論斷,就是微觀的書(shū)道。“書(shū)”,實(shí)屬?lài)?guó)學(xué),無(wú)可非議,只是后來(lái)的書(shū)者,在“以書(shū)取仕”、“以書(shū)謀利”的時(shí)代背景下,為追求功名利祿,專(zhuān)注技藝,而抽空了書(shū)法及其育人的人文內(nèi)涵。《書(shū)法?國(guó)學(xué)》的獨(dú)一味,說(shuō)白了,只是在追求書(shū)法及其教育的本真而已。然而她是值得敬重的,畢竟在我國(guó),尤其在我國(guó)的新時(shí)代,書(shū)法及其教育的路子基本上還是弄歪了的老“書(shū)道”。何也?眼光的局限,看不到書(shū)法藝術(shù)的生命走向——記事?tīng)钗锏姆?hào)功能日趨衰老,傳播文人的功能日益勃發(fā)。
扉頁(yè)中,由連續(xù)四個(gè)分判斷組成的一個(gè)總判斷,道出了新時(shí)代書(shū)法的本質(zhì),真叫人我耳目一新;封底上兩段陳述或兩段祈使,闡明了新時(shí)代書(shū)法教育的書(shū)道,催我登上了一個(gè)新臺(tái)階!
深度,獨(dú)一味。
深度,怎么理解,如何測(cè)量?我以為用精微的舉措直抵預(yù)設(shè)的目標(biāo)。深度取決于精微。只有“精”,才能深;只有“微”,才能達(dá)到“度”。從物理學(xué)的角度講,受力面積小,壓強(qiáng)才越大。
讀書(shū),我有點(diǎn)小經(jīng)驗(yàn):有高度的東西往往表現(xiàn)在概念的構(gòu)建,而缺乏精微的演繹。就像我們見(jiàn)到牛肉罐頭,而沒(méi)看到給牛喂草、治病,宰牛取肉、調(diào)味裝罐等辛苦步驟一樣,好看好吃卻不知其個(gè)里。而《書(shū)法?國(guó)學(xué)》卻個(gè)里分明,體現(xiàn)了教科書(shū)(校本教材)的特質(zhì)——精嚴(yán)細(xì)實(shí),深度恰好。
單元目錄中,有《筆畫(huà)——‘神’所致》《筆法——‘智’所用》《結(jié)體——‘仁’所以》等題標(biāo)。我就想,筆畫(huà),不就是點(diǎn)、橫、撇、捺等構(gòu)成漢字的基本部件,怎么會(huì)牽扯到“神”呢?筆法,不就是運(yùn)筆書(shū)寫(xiě)的技法,與“智”又何以相干?結(jié)體,原本就是由字素組成字的玩兒,豈有“仁”哉?
作品構(gòu)思可謂精微,我也不得不精微一下。
僅以第三單元為例。筆法篇——“智”所用,先用詩(shī)的語(yǔ)言作【引子】,總攬全局,給學(xué)生一罐“牛肉罐頭”;然后以《中以立骨屋上梁》《側(cè)以出艷綿裹鐵》《藏頭護(hù)尾美如蠶》《出鋒顯勢(shì)劍出鞘》等七個(gè)課目來(lái)支撐,使讀者在各種常用筆法中感受到了中華民族的多種智慧。
開(kāi)篇我提出了疑問(wèn):筆法,不就是運(yùn)筆書(shū)寫(xiě)的技法,與“智”又何以相干?讀了這里,我已疑慮冰釋。《藏頭護(hù)尾美如蠶》是這一單元的第三課,先由書(shū)法爺爺講了個(gè)斗雞的故事,接著用幾幅圖片讓讀者感知理解“藏頭護(hù)尾”的筆法,并歸納其要領(lǐng)——“藏鋒起,逆鋒收,藏頭護(hù)尾一筆就。似蠶頭,如蠶尾,畫(huà)在字中美個(gè)夠。”這一歸納,如詩(shī)如詞,很好理解。要是我還說(shuō)三道四,就可能破壞了它的原汁原味。
作者如果就此擱筆,學(xué)國(guó)學(xué),學(xué)做人就不能體現(xiàn)出來(lái)。他在策劃中匠心獨(dú)運(yùn),來(lái)了個(gè)《媽媽的嘮叨》:“孩子,爺爺《紀(jì)渻子馴斗雞》的故事告訴我們,真正有才能的人,往往深藏不露,不會(huì)顯擺自己。《老子?八章》上說(shuō):‘上善若水,水善利萬(wàn)物而不爭(zhēng)。’所以我們?yōu)槿颂幨溃獌?nèi)斂含蓄,即使具備了高尚的品德和高超的技能,也不要過(guò)于張揚(yáng)。你看,被紀(jì)渻子訓(xùn)練出來(lái)的斗雞,表面傻乎乎,但內(nèi)里精明強(qiáng)大;其它斗雞表面威武雄壯,可就是不敢靠近半步。 ‘藏頭護(hù)尾’是東漢書(shū)法家蔡邕在《九勢(shì)》里的書(shū)法秘笈之一。它要求我們:在書(shū)寫(xiě)漢字的某些筆畫(huà)的某些部位時(shí),多用藏鋒,少用出鋒。我們中國(guó)人做人做事,不要鋒芒外露,要引而不發(fā)!我們?cè)趯W(xué)校讀書(shū),不要有了點(diǎn)成績(jī),生怕老師和同學(xué)們不知道,到處張揚(yáng);要謙虛謹(jǐn)慎,練好硬功夫!”
媽媽的話(huà)實(shí)屬“嘮叨”,但嘮叨得好啊!她本著“形相似,意相聯(lián)、理相通”的原則,把學(xué)書(shū)法、學(xué)國(guó)學(xué)、學(xué)做人三者的道理相勾連,形成了有機(jī)整體,且毫無(wú)牽強(qiáng)附會(huì)之感。
“中國(guó)智慧何處覓?
筆法,就是中國(guó)智慧集散地——
中立骨,側(cè)出艷,藏頭護(hù)尾堪稱(chēng)賢。
提與按,徐與疾,度的把握分寸間。
公主與擔(dān)夫爭(zhēng)道,白鵝與河水競(jìng)游,筆筆轉(zhuǎn),畫(huà)畫(huà)美。
枯筆潤(rùn)筆巧配合,律呂調(diào)和,閏余成歲??????
讀得懂是智慧,用得好是智慧,顯得出也是智慧——
筆畫(huà)貫通氣韻,筆法彰顯智慧!”
這是本單元【引子】中的一段話(huà)。讀完這一章,我本想再啰嗦幾句,但又覺(jué)得她實(shí)在可口可心可目,便“借代”一下,權(quán)當(dāng)我心一得,做個(gè)點(diǎn)贊的理由。
寬度,獨(dú)一味。
高度,體現(xiàn)在作者的境界和作品的立意——站在國(guó)學(xué)、育人的高度,鳥(niǎo)瞰書(shū)法秘笈;深度,體現(xiàn)“書(shū)意轉(zhuǎn)深”——筆法,乃中國(guó)智慧的集散地。而寬度又該指什么呢?
第四單元題標(biāo)為“結(jié)體——‘仁’所依”。這里同樣有個(gè)【引子】——
“二人相處便成仁,
單筆獨(dú)畫(huà)字難成。
結(jié)體猶如人相處,
一個(gè)仁字主其間。
依于仁,避讓有禮;
依于仁,排疊有序;
依于仁,頂戴有義;
依于仁,借代不分我你;
依于仁,穿插可破千重壁;
依于仁,包圍、顧盼猶如親兄弟。”
這個(gè)引子好啊!詩(shī)性語(yǔ)言,抓住“仁”字這個(gè)綱,用七個(gè)排比句,像漁家姑娘撒網(wǎng)一樣,“網(wǎng)落金波閃,網(wǎng)起笑聲脆”,把避讓、排疊、頂戴、借代、穿插、包圍、顧盼等常見(jiàn)的幾條“魚(yú)”一一撈了上來(lái);又像太陽(yáng)公公一樣,毫不吝嗇地由一個(gè)圓心引發(fā)出若干射線(xiàn),把光芒射向書(shū)法結(jié)體的所有關(guān)節(jié)。
“仁”,從字形上看,左“亻”右“二”,即可得意一二——“二人相處便成仁”,二人相處需要仁。不是嗎??jī)扇嘶騼扇艘陨系娜讼嗵帲蜁?huì)發(fā)生各種各樣的關(guān)系。這些關(guān)系可以是國(guó)與國(guó)之間、民族與民族之間、行業(yè)與行業(yè)之間、師生之間、夫妻之間、鄰里之間、同事之間、同學(xué)之間、兄弟姊妹之間等等。無(wú)論何種關(guān)系都需要“仁”來(lái)維系,不然就矛盾重重,甚至烽煙四起,社會(huì)就不太平,各種關(guān)系就不能和諧。
書(shū)法結(jié)體也一樣,兩個(gè)或兩個(gè)以上筆畫(huà)結(jié)體成字,也會(huì)發(fā)生各種關(guān)系。這些關(guān)系要處理好,依然少不了“仁”!但書(shū)法結(jié)體的形式猶如人與人之間的關(guān)系一樣,錯(cuò)綜復(fù)雜且多變,一個(gè)“仁”字怎能了得?《書(shū)法?國(guó)學(xué)》一書(shū)就能漂亮地了得。這就是她的寬度所在!你看“依于仁,避讓有禮;依于仁,排疊有序;依于仁,頂戴有義;依于仁,借代不分我你;依于仁,穿插可破千重壁;依于仁,包圍、顧盼猶如親兄弟。”
由孔子提出,孟子、董仲舒相繼延伸為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的“五常”,乃中華民族的人際關(guān)系學(xué)和為人處事最基本的準(zhǔn)則。但居于“五常”之“首”的“仁”與“義、禮、智、信”之間又是什么關(guān)系呢?首都,乃一國(guó)之都;首長(zhǎng)乃群中之王;首席乃活動(dòng)中擔(dān)綱之人。由此而推斷,“仁”乃“五常”之總統(tǒng),如手掌與手指。無(wú)掌,指無(wú)依;無(wú)指,掌將不掌。換言之,你對(duì)人不義、無(wú)禮,處事缺心少眼,不講誠(chéng)信,能說(shuō)你“仁”嗎?
高度、深度、寬度的獨(dú)一味,我分開(kāi)來(lái)說(shuō),是為了行文的方便,絕不意味著三者分家。它們之間就像月亮與月暈一樣,不能絕對(duì)分開(kāi)。理解時(shí)既要看到月亮,也要關(guān)注月暈!
可讀,獨(dú)一味。
食品添加劑,很多人談虎色變,是因?yàn)檫^(guò)度使用;但在食品中添加了它,味道就是討人喜歡。好的作品讀起來(lái)舒服,消化也快;孬的讀物讀起來(lái)受罪,很難吸收。原因在哪里,其中一個(gè)重要因素或無(wú)“添加劑”或“添加劑”使用不當(dāng)。
《書(shū)法?國(guó)學(xué)》,我是一口氣讀完,還能寫(xiě)點(diǎn)東西出來(lái),除了有“花香”的優(yōu)雅環(huán)境,更有“書(shū)香”的誘惑啊!
我是以教書(shū)謀生的“老教鞭”,教科書(shū)見(jiàn)過(guò)不少。總體感覺(jué)大都像大雄寶殿里高高在上的“神雕”——木然、莊重、威嚴(yán),不容許你面帶笑容。此書(shū)也是教科書(shū),可味道就是獨(dú)特,很是逗人喜歡。
本作品的香味,在于高度、深度、寬度的特別,還在于可讀度的非常。為什么?有謎語(yǔ),有故事,有笑話(huà),有童話(huà),有詩(shī)歌,有圖畫(huà)等人們喜聞樂(lè)見(jiàn)的“添加劑”,能把那古老的書(shū)法話(huà)題演繹得正正規(guī)規(guī)、活活美美,既像鐘繇筆下的楷書(shū),又像張旭飆墨而成的狂草。
請(qǐng)看:
“一截竹管,一撮雜毛,奇葩婚配傳道。”
這是“常識(shí)篇”第一課中“筆”的謎面,由作者原創(chuàng)。“文房四寶”之一的毛筆,基本上是竹管與禽獸之毛結(jié)合而成。作者把這種結(jié)合稱(chēng)為“奇葩婚配”,真令人叫絕。不是嗎?竹子和禽獸之毛,原本是有生命的,只是它們這時(shí)都“死”了,不懂得婚配。但經(jīng)秦國(guó)大將蒙恬的牽線(xiàn),二者婚配,且能“傳道”。男女婚配有傳宗接代的偉大,竹管與雜毛的婚配有“傳道”的宏績(jī)啊!社會(huì)與自然間的種種規(guī)律不正是由筆記下,又一代一代往下傳的嗎?
其實(shí)要說(shuō)明“筆”,很簡(jiǎn)單,實(shí)物往學(xué)生面前一晃,筆字往黑板上一寫(xiě),干凈利落、明明白白了事也未尚不可;然而學(xué)生能獲得這么多有益有趣的知識(shí)嗎?只怕獲得的只是雜毛一撮,空管一截,人也可憐,筆也可憐!
再請(qǐng)看:
“古時(shí),有位縣太爺寫(xiě)了個(gè)紙條(豎著寫(xiě))要仆人去買(mǎi)‘豬舌燒’了下酒,可他把舌字上面‘千’的一豎寫(xiě)長(zhǎng)了,成了‘豬千口’。結(jié)果是小酒沒(méi)喝成,仆人挨罵,縣太爺也羞得無(wú)地自容(一下子到哪里去買(mǎi)一千頭豬呢)。”這是“結(jié)體篇”第四課“穿插”內(nèi)容中書(shū)法爺爺講的故事。故事生動(dòng)形象有趣,一下就讓讀者明白:書(shū)法結(jié)體忌諱松散。這比有些人對(duì)這點(diǎn)知識(shí)一千遍的闡釋好一萬(wàn)倍。痛快!
還請(qǐng)看:
“固國(guó)四周有長(zhǎng)城,
包涵同道勿閉門(mén)。
包者必定心胸寬,
全包半包皆靠仁。”
這是結(jié)體篇對(duì)“包圍”結(jié)構(gòu)要點(diǎn)的小結(jié)。四句話(huà)二十八個(gè)字,可內(nèi)容極其豐富。有包圍結(jié)構(gòu)的例字(固、國(guó)、四、周、包、涵、同、道、勿、閉、門(mén)),既有全包,又有半包;有愛(ài)國(guó)、愛(ài)人的思品滲透——鞏固國(guó)防四面要有長(zhǎng)城;包涵志同道合的人,不要關(guān)上門(mén);能夠包容人的人要心胸開(kāi)闊;如何才能包涵他人,無(wú)論全包或半包都要有“仁”心。整體一語(yǔ)雙關(guān),比喻貼切。
我細(xì)細(xì)地統(tǒng)計(jì)了一下,這本書(shū)中謎語(yǔ)28個(gè),基本屬于作者原創(chuàng);故事25個(gè),個(gè)個(gè)有根,根在統(tǒng)文化中的經(jīng)典,如“昭君出塞”、“蘇武牧羊”等;詩(shī)詞32首,是詩(shī)又是詞,是詞又是詩(shī),均屬原創(chuàng)。
除此之外,每一具體課目皆設(shè)《書(shū)法爺爺講故事》《書(shū)法要點(diǎn)》《國(guó)學(xué)語(yǔ)錄》《媽媽的嘮叨》《我和筆筆臨墨池》小版塊,且都圍繞學(xué)書(shū)法、學(xué)國(guó)學(xué)、學(xué)做人這個(gè)中心展開(kāi)。這一設(shè)計(jì),可見(jiàn)作者把自己置身于智的山、花的海和心的玉壺。我可推斷:他(她)就是人類(lèi)靈魂的工程師!不然,他怎能猜度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個(gè)性呢?“爺爺?shù)暮永镩L(zhǎng)滿(mǎn)了故事”;“媽媽準(zhǔn)備了一席嘮叨”;“我”可能是個(gè)喜歡與“筆筆”為伴的青少年;老師始終沒(méi)有出場(chǎng),卻能感受到笑容可掬的老師就在身邊。
我本想就此擱筆,卻按捺不住,還請(qǐng)欣賞如下設(shè)計(jì)——
“我看:
——光澤柔和,無(wú)草梗,無(wú)沙粒,無(wú)洞眼。
我摸:
——光滑,細(xì)膩,厚薄勻。
我抖:
——綿軟,不脆,聲細(xì)綿。
我試:
——吃墨快,擴(kuò)散勻,分層涂墨層次清。”
這是指導(dǎo)讀者識(shí)別紙張優(yōu)劣的內(nèi)容。作者沒(méi)有將其要領(lǐng)硬塞給讀者,而是要求他們通過(guò)感知去識(shí)別——“我看”、“我摸”、“我抖”、“我試”。說(shuō)心里話(huà),用紙,我還真不知道這樣做呢!哎,這哪里只是教本,不就是很好的教案嗎?
味獨(dú)一,意綿長(zhǎng),恕我不能一直說(shuō)下去!最后哼一小曲——
書(shū)道千古長(zhǎng),人文之絕唱。
命運(yùn)卻多舛,志士敢救亡。
新時(shí)避古道,創(chuàng)新要擔(dān)當(dāng)!
注:本網(wǎng)發(fā)表的所有內(nèi)容,均為原作者的觀點(diǎn)。凡本網(wǎng)轉(zhuǎn)載的文章、圖片、音頻、視頻等文件資料,版權(quán)歸版權(quán)所有人所有。